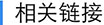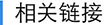首頁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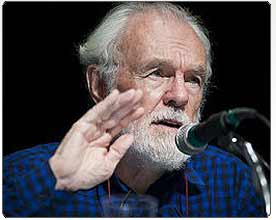 我寫《資本的限度》(后簡稱《限度》)是為了爭取使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思想更加容易讓人理解,更加切合那個時代的具體問題。那是20 世紀70 年代,“全球化”“金融衍生品”和“對沖基金”這樣的詞還不在我們的詞匯表里,歐元和世界貿易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這樣的組織還只是白日夢,而且有組織的勞工和實質性的(而非名義上的)左翼政黨仍然在特定的民族國家看似牢固的框架中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在《限度》成書時,撒切爾(Thatcher)和里根(Reagan)尚未掌權,中國尚未開始推行令人震驚的改革開放政策,一切事物的金融化還顯得不正常,外包和資本在全球的機動性還沒有開始在某些方面嚴重挑戰民族國家調節自身事務的主權力量。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資本家階級所發起的攻擊——它針對的是工人階級的力量、福利國家和一切形式的國家調節——還處在早期,僅見于局部,并未成熟且四處擴散。本書的寫作還遠遠早于“冷戰”的結束、原共產主義經濟體的“市場化”、對共產主義的全盤質疑和對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的國家干預主義理論的廣泛拒斥。簡言之,本書早于新自由主義反革命(neoliberal counterrevolution)的發動。
我寫《資本的限度》(后簡稱《限度》)是為了爭取使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思想更加容易讓人理解,更加切合那個時代的具體問題。那是20 世紀70 年代,“全球化”“金融衍生品”和“對沖基金”這樣的詞還不在我們的詞匯表里,歐元和世界貿易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這樣的組織還只是白日夢,而且有組織的勞工和實質性的(而非名義上的)左翼政黨仍然在特定的民族國家看似牢固的框架中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在《限度》成書時,撒切爾(Thatcher)和里根(Reagan)尚未掌權,中國尚未開始推行令人震驚的改革開放政策,一切事物的金融化還顯得不正常,外包和資本在全球的機動性還沒有開始在某些方面嚴重挑戰民族國家調節自身事務的主權力量。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資本家階級所發起的攻擊——它針對的是工人階級的力量、福利國家和一切形式的國家調節——還處在早期,僅見于局部,并未成熟且四處擴散。本書的寫作還遠遠早于“冷戰”的結束、原共產主義經濟體的“市場化”、對共產主義的全盤質疑和對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的國家干預主義理論的廣泛拒斥。簡言之,本書早于新自由主義反革命(neoliberal counterrevolution)的發動。
然而,《限度》變成了一個預言性的文本。現在它在某些方面尤為重要,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它所繪制的理論路徑來抓住新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在運作時固有的矛盾。它的當代意義的上升有幾個原因。第一,馬克思的主要政治經濟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批判經典的自由主義理論(特別是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這種批判方法同樣適用于主張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后者主要源自18 世紀的自由主義,并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義做了修改(這些教義拋棄了勞動價值理論,贊同邊際主義原則,由此為無盡地闡述關于市場如何運作的理論開辟了道路)。馬克思的批判手法用在新自由主義身上遠遠比用在“內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和凱恩斯主義身上更加適合——后兩者在20 世紀70 年代中期之前支配了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
第二個原因出現得相當湊巧。為了理解城市化的過程——當時我的興趣直接聚焦在這上面——我需要擴展馬克思的一些未經展開的范疇。固定資本[特別是內嵌于建成環境(builtenvironment)的固定資本]、金融、信用、租金、空間關系和國家開支必須全部放到一起,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化過程、房地產市場和不平均的地理發展。從這里產生的理論工具非常適合于應對后來出現的戲劇性的全盤變革。所以,我其實構造了一個強健的理論基礎,可以用來批判性地探討一個由金融引導的全球化過程到底意味著什么。《限度》試圖在馬克思的論述的總體框架中以整體主義的和辯證的方法,而不是分割的和分析的方法來把資本積累的金融方面(時間性)與地理方面(全球性和空間性)整合起來;它曾經是——至今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這樣做的文本。它在基礎理論(在這方面有許多出色的、相互抗衡的闡述)與實實在在的力量的表達之間給出了一種系統性的聯系。
第三個原因具有更為直接的政治性。20 世紀70 年代充滿了紛爭。當時呈現出來的資本積累的全球危機是20 世紀30 年代以來*糟糕的一次。強勢的國家干預主義陷入了困境,盡管它在1945 年之后流行于大多數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并帶來了較高的增長率。由1973 年中東戰爭所引發的石油禁運標志著衰退的開始,而且提出了一個問題:流入海灣國家的石油美元如何能通過金融體系回到全球經濟當中。1973 年初發生的世界性房地產暴跌、多家金融機構的同時倒閉以及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協議的解體——這些都帶來了令人迷惑的問題。已經有人把去除金融調節和預算緊縮作為解決方案來販賣(特別是在美國,一個城市發生的事件——紐約市在1975 年實行的財政規訓——起到了帶頭作用)。英國在1975—1976 年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懲戒,智利則隨著1973 年皮諾切特(Pinochet)針對阿連德(Allende)的政變而走向了新自由主義。勞工的動亂四處蔓延,左翼政治運動在歐洲和發展中世界的許多地區也都取得了進展。就連在美國,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和學生運動也聯合起來攪動著政治體系,威脅著政治經濟精英,也威脅著公司和國家的合法性。簡言之,資本積累出現了普遍化的危機,資本家的階級權力也遭到了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