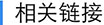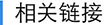首頁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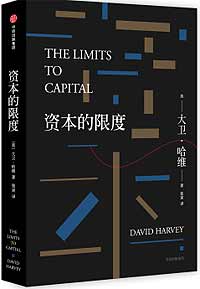 在20 世紀70 年代的混亂中勝出的解決方案(盡管各處的勝負是非常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或所謂“自由市場”的路線,其中帶頭的是金融資本(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美元的問題)。這次勝利絕不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沒有它自身內在的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矛盾和不穩定性——后一點如今已經極為明顯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個實在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在《資本論》第1 卷,馬克思證明了一個社會越是符合去除國家調節的自由市場經濟,權力的不對稱——有的人擁有生產資料,有的人則被排除在生產資料所有者之外——就越會造成“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而“在另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資本論》第1 卷,第645 頁)1。30 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結果。我們可以構造一種可信的論證——我在《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Neoliberalism)2 中試圖說明這一點——資本家階級的主導派系之所以會提出新自由化的日程,從最開始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結果。從20 世紀70 年代的亂局中興起的資本家階級精英分子恢復、鞏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構了他們在全世界的權力。
在20 世紀70 年代的混亂中勝出的解決方案(盡管各處的勝負是非常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或所謂“自由市場”的路線,其中帶頭的是金融資本(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美元的問題)。這次勝利絕不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沒有它自身內在的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矛盾和不穩定性——后一點如今已經極為明顯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個實在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在《資本論》第1 卷,馬克思證明了一個社會越是符合去除國家調節的自由市場經濟,權力的不對稱——有的人擁有生產資料,有的人則被排除在生產資料所有者之外——就越會造成“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而“在另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資本論》第1 卷,第645 頁)1。30 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結果。我們可以構造一種可信的論證——我在《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Neoliberalism)2 中試圖說明這一點——資本家階級的主導派系之所以會提出新自由化的日程,從最開始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結果。從20 世紀70 年代的亂局中興起的資本家階級精英分子恢復、鞏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構了他們在全世界的權力。
這次政治轉變——階級權力的恢復和重構——意義重大,需要更加詳細地予以評論。階級權力本身是含糊的,因為它是一種難以直接衡量的社會關系。但它的行使需要一個看得見的必要條件(盡管絕不是充分條件),即收入和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的積累。這些積累和積聚的存在直到20 世紀90 年代中期都得到了聯合國報告的廣泛關注。當時人們發現,世界上最富有的358 個人的資產凈值“等于世界上最貧困的45% 的人口——共計23 億人——的收入總和”。世界上最富有的200 個人“在到1998 年為止的四年間使他們的資產凈值翻了一倍有余,超過了1 萬億美元”,因而“世界的前三名億萬富豪的資產超過了所有最不發達國家及其6 億人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這些趨勢一直在加速,盡管各處的加速并不平均。在美國,前1%的收入賺取者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從1980 年到2000 年翻了一倍有余,而前0.1% 的人達到了原來的三倍有余。從1972年到2001 年,“從低往高第99 個百分位的收入增長了87%”,而“第99.9 個百分位的收入增長了497%”。在1985 年的美國,《福布斯》400 富豪的財富總和在按照通貨膨脹予以調整之后“為2380 億美元”,“平均資產凈值為6 億美元”。到了2005 年,他們的平均資產凈值則是28 億美元,全部資產達到了1.13 萬億美元——“超過了加拿大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轉變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管薪酬的急速上升。“按照今天的美元來計算,普通的首席執行官在1980 年可以掙160 萬美元年薪”,但到了2004 年,年薪數字上升到了760 萬美元。布什(Bush)當局的稅收政策令人憤慨地使這些差別更加懸殊了。稅收減免的大多數好處都流向了前1% 的收入賺取者,而且最近的稅務法案只為“處于收入分配中段的人”削減了大約“20 美元”的稅負,而“前1% 的人當中的前十分之一盡管有530 萬美元的平均收入,卻平均可以省下82415 美元”。這些趨勢并不局限于美國。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只要新自由主義政策掌權了——這些政策在地理上的擴散是非常不平均的——收入和財富極其懸殊的差距就會隨之出現。在1988 年之后的墨西哥,隨著私有化和經濟結構轉換的浪潮,有24 名墨西哥億萬富豪出現在了1994 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排在第24 位。在2005 年,嚴重貧困的墨西哥擁有了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億萬富豪。在俄羅斯以“休克療法”實行市場改革的幾年間,七名寡頭控制了近一半的經濟。隨著市場改革,東歐和中歐也同樣顯示出了不平等程度的劇增。由于瑪格麗特·撒切爾在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推動,前1% 的收入賺取者到2000 年為止已經把他們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翻了一倍。東亞和東南亞的所謂“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最初還能夠把強勁的增長與合理的分配平等結合起來(如韓國),但自1990 年以來——主要是在它們的經濟遭受了1997—1998 年猛烈的金融沖擊之后——它們的不平等程度卻出現了45% 的增加。在印度尼西亞,少數貿易巨頭的大筆財富避開了這場創傷的侵害,卻有大約1500 萬印尼人失業。
(文章摘自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資本的限度》,作者:[英] 大衛·哈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