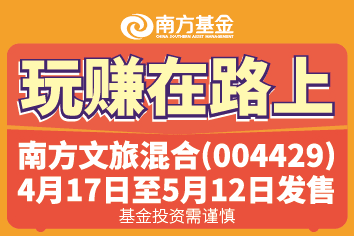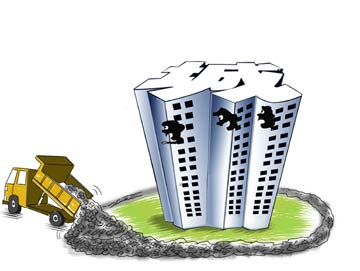互聯網越來越迅猛地切入中國經濟的各個方面,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為代表,這一輪新技術革命催生了大量就業崗位。一方面,互聯網與制造、能源、材料等傳統領域不斷融合發展,創造出更加多樣和靈活的新職業,另一方面,眾多分享經濟平臺培育了規模巨大的自由就業群體。在這幅不斷變遷的就業版圖上,新勞動者紛紛登場。五一國際勞動節將至,《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幾位不同領域的新勞動者,記錄下他們在這輪產業大變革中的身影。
鏖戰高峰的共享單車調度員
□記者 王奇/北京報道
地處北京西單商圈的靈境胡同地鐵站,是胡貴林最常出現的工作地點。這個來自四川的90后小伙子,目前在一家公司負責共享單車的調度協調工作。幾乎每天上下班高峰時,他都會出現在他所負責區域內共享單車告急的交通站點。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靈境胡同地鐵站遇到胡貴林時是早上八點半左右,目光所及之處不見一輛可用的共享單車。胡貴林告訴記者,工作日的早上,這里都會出現用車高峰,很多金融街的上班族,下了地鐵后使用共享單車完成上班路途的“最后一公里”。
沒過多久,一輛載滿共享單車、用于調度的電動三輪車駛來。車剛停穩,就被伸長手臂競相掃描二維碼開鎖的人們團團圍住。胡貴林緊忙上前一塊卸車。此后約40分鐘時間里,幾輛調度車周而復始跑了十多趟,每次都是滿載而來、空車離去。
“金融街、中關村等繁華商業區附近的調度工作最為繁忙,這些地區上班人流大,對共享單車的需求量非常大。”胡貴林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公司負責一家共享單車公司在北京一些城區的單車調度工作,在他所負責的西城片區,目前有幾十輛調度車,根據調度員在街上的巡視情況和系統的定位數據展開具體的調度工作。每輛調度車每天大概要跑十來趟,運送單車超過百輛。
北京市交通委數據顯示,自去年8月以來,ofo、摩拜、小藍、酷騎、永安行、智享等企業先后在北京投放共享自行車近70萬輛。盡管投放量巨大,但胡貴林表示,高峰時段熱點地區共享單車仍“供不應求”。如記者所見的調度車一到單車即被“搶光”的景象司空見慣,有些著急用車的人,甚至等不及調度員動手,直接“自助”卸車。
記者看到,盡管一些搭乘地鐵的人不斷將共享單車“自然循環”到這里,但時至上午十一點左右,站點前的停放區域始終沒有閑置的單車。
“五一”假期將至,胡貴林和同他并肩“作戰”的幾十位調度車駕駛員即將迎來一場“硬仗”。他說,周末和節假日也是他們工作的高峰期,熱門景點附近成為共享單車的密集停放區,不規范停放問題更為突出。“希望大家都能把共享單車停放到指定的區域,規范停車,是為了交通安全,也是為了大家能夠更好地用車。”
植保無人機飛手養成記
□記者 王婧 王龍云/北京報道
張鏑從事無人機植保工作不過一年,已是一支由42名飛手組成的無人機植保隊隊長了。談及這個新興行業,正在山西省臨汾市吉縣進行蘋果樹植保作業的他,流露出發自內心的激情。
張鏑清楚地記得,去年內蒙古一處葵花田染病時農戶們在路邊迎接植保隊到來的情形。葵花生病后,農戶難以進入密密麻麻的葵花田進行人工噴灑農藥,幸好無人機植保隊及時解決了難題,消除了絕收的危險。“與傳統植保方法比,無人機植保具有很多明顯的優勢,不僅可以大大降低人工等成本,還可以提高農藥利用效率。”張鏑說。
在接觸農業科技這個領域前,1987年出生的張鏑曾做過財務工作,還領著一支20多人的物流團隊干過礦石運輸。后來,張鏑在內蒙古的農業科技企業禾文科技從事無人駕駛拖拉機導航等技術的代理工作。
直到去年5月,張鏑才開始接觸無人機植保工作。一開始,張鏑并沒有把操控無人機當成一回事,以為這只是很簡單的活兒。沒想到,第一次操控無人機就碰到了“炸機”事故(無人機撞到障礙物)。眼瞅著無人機一頭撞到樹上,“傷”得不輕。張鏑懊惱了很久。當年11月,他參加了大疆的無人機飛手培訓項目,畢業后成為一名專業的植保無人機飛手。從此,張鏑帶領一支無人機植保團隊,在內蒙古多地進行無人機植保作業。
作為一個身處一線的飛手,張鏑認為,目前國內無人機植保市場需求巨大,遠遠得不到滿足。在他看來,現在市場上的植保需求連1%都難滿足。張鏑說,目前他的團隊也在努力向更多農戶尤其是種植大戶推廣無人機植保。
談到2017年,張鏑對這個新興行業的發展充滿了信心,他計劃將自己的團隊進一步擴大,再招收20名飛手,增加20臺無人機。張鏑同時表示,團隊的擴充并非一味強調數量和規模,對于飛手的資質必須嚴格把關。
輿情分析師,不“雜”無以“專”
□記者 鐘源/北京報道
每天瀏覽成百上千個網頁,對突發公共事件和熱門話題如數家珍,熟知網絡流行語和熱門段子,迅速把握熱點,準確分析輿情,預測輿論走勢,有效化解危機,這是一個網絡輿情分析師的普通一天。對于已經入行近十年的輿情高級分析師王超來說,上述的每一個環節都已得心應手。
王超目前供職于一家北京的咨詢公司,該公司主要為客戶提供針對性的數據搜集、分析、研究和咨詢服務,曾為眾多知名跨國公司以及優秀的國內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過市場研究服務。
據王超介紹,他一般按日、周、月、季度和年定期向客戶發報告,有時也發一些臨時機動的突發消息。“一般政府機構和行業內比較成熟的大品牌公司,對輿情比較關注。比如我以前服務的上海大眾汽車,每天網上涉及該公司的信息非常多,不可能每條都發給他們,即便都發過去,客戶也不一定顧得上看。所以我們需要挑一些當天比較重要的信息,比如客戶一般比較關注發稿量比較多、涉及負面的信息,以及對行業影響較大的政策性信息。”他說。
“輿情行業說簡單也簡單,只需網上搜集些材料匯總就行,但是如果你想為客戶提交一份非常專業、高質量的報告。它需要從業者是個‘雜家’,除最基本的數據統計外,還需要懂一點公關學、營銷學、傳播學等,彼此要融會貫通。”王超告訴記者,他在大學學的是計算機專業,現在在學習其他專業,“這個行業雖然門檻不高,但也不是簡單的拼體力,我有一定的工作經驗,未來還想在專業性和管理上有所發展”。
西藏老司機的朋友圈生意經
□記者 趙東東/拉薩報道
往上是綠植覆蓋的峭壁,往下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深澗,蜿蜒迂回的川藏公路被認為是中國路況最險峻、

通行難度最大的公路,而與之相伴的是驚險壯美的景觀以及“隔山不同天,一天有四季”的奇妙體驗。可以說,對于經陸路由川進藏的游客來說,沿川藏公路自駕游是一種危險的誘惑。不過,若有幸通過微信朋友圈找到老姚當代駕,欣賞沿途的美麗風景便會變得安全愜意。
老姚,大名姚振松,河南許昌人,2001年進藏到拉薩開起出租車,現在的身份是西藏林芝藍天汽車租賃有限公司的老板,在藏十幾年的駕齡讓他成為名副其實的老司機,一位載著游客飽覽西藏大好河山的老司機。
“拉薩通火車后,到西藏的游客越來越多,覺得里面存在商機,2007年便轉行干起針對旅游市場的汽車租賃業務。當然,一開始也不好干。”老姚回憶起當初轉行的經歷時,口氣頗有些見證歷史的滄桑感。“熟悉西藏的人都知道,林芝地區旅游資源豐富,有巴松措、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南迦巴瓦峰、魯朗特色小鎮等著名景點,再加上當地海拔相對較低,氣候宜人,很多進藏游客都會到此一游,所以選擇了林芝作為自己的大本營和公司所在地。”
頭腦靈活加上勤奮努力,經過一番摸爬滾打之后,老姚的租車業務慢慢步入正軌,很多進藏的游客會到他掌舵的汽車租賃公司購買出行服務。目前,老姚的公司已經有十幾臺自有車輛,駕駛員八人。
當老姚的租車業務乘著西藏旅游市場的東風越做越大時,互聯網的發展,尤其是微信等社交媒體的興起,讓老姚的生意更上一層樓。老姚除了在58同城、趕集網上發布廣告信息外,在百度上直接搜索公司名也可以找到他,而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微信朋友圈更成為老姚重要的業務來源。“有些游客感覺我們服務還行就加了微信,他們會在朋友圈發布旅游乘車的體驗,通過口碑傳播,就會有其他游客找到我們。”他說。
據老姚稱,他們公司在線上和線下提供的服務主要包括兩種,一是代駕,一些平原地區的司機進藏之后不熟悉路況,有的司機害怕走山路,便會找人代駕;二是連人帶車一起“出租”,“我們的司機保證駕駛技術過硬且熟悉路況,定期檢測的自有車輛更是成為安全的保障”。
由于服務好并借助互聯網拓展客源,老姚的業務在短短幾年內覆蓋了整個西藏地區,西藏的著名景區和交通要道都曾閃過老姚專注開車的身影。在業務快速拓展的同時,老姚公司員工的收入也節節高。“一個人一臺車,一年大概有十幾萬的收入吧。”老姚說。
作為一名有十幾年駕齡的老司機,老姚不僅車技嫻熟,行萬里路的經歷也讓他成為一名見多識廣的旅游向導。在給游客開車時,他經常會講起各個自然景觀的看點和人文景觀的歷史典故。由于經常在野外行車,老姚的皮膚已變成古銅色,臉上如當地藏民一般淳樸憨厚的笑容成為他的標志表情。
“當然想多養幾個人和幾臺車,那樣才能掙更多的錢。不過,汽車租賃市場競爭壓力大,只有靠服務和口碑才能贏得游客的認可。”當問及是否有擴展公司規模的想法時,45歲的老姚充滿憧憬地說。
“碼字三年,始知新媒深似海”
□記者 楊燁/北京報道
28歲的張灝然自2014年碩士畢業后入職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參與“國資小新”新媒體平臺的運營已三年。這個待人溫厚的小伙子如今仍喜歡稱自己是“新兵”,用他的話說,“辛勤碼字整三年,始知新媒深似海”。

“新媒體工作究竟是什么?我愿意用三句話來概括。”張灝然說,第一句話,新媒體是技術驅動型領域,不斷更新、不斷升級是常態。
微博、微信、客戶端,VR、直播、短視頻,機器人寫作、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近年來,新技術潮流涌動,新業態風口頻出,隨之而來的是新媒體從業者一遍遍經歷迷惑、痛苦、適應、創新、再迷惑的循環。
張灝然說,新的技術和應用,如何轉化為用戶實實在在可觸及的內容和服務,是包括新媒體人在內的互聯網從業者一貫的使命。沒有確定性,是這個行業最大的確定性;快速獲取知識的渠道、將技術合理應用于內容生產的腦子,是這個行業最寶貴的資源之一。從這個角度講,新媒體人有點像“情報員+產品經理”。
他表示,技術在更新換代,新媒體人也會自我升級。“以我們所運營的國資委新聞中心的官方新媒體平臺‘國資小新’為例,用H5頁面立體呈現‘一帶一路’上中國企業的重大建設成就,通過直播帶領粉絲探訪‘蛟龍號’深海載人潛水器,以VR展現港珠澳大橋的宏偉壯觀……都是前沿技術應用的典型案例。只要有‘吃螃蟹’精神,技術就不會成為新媒體人的挑戰,而是創作新內容、提供新服務、破除既有瓶頸的大好機遇。”
第二句話,新媒體是勞動驅動型領域,全情投入、追求極致是本分。張灝然告訴記者,新媒體的生存之道,一為“快”,熱點事件發生后,迅速響應,或披露信息,或事件營銷;一為“奇”,根據用戶的興趣愛好和自己的專業優勢,提供獨一無二的視角和內容。歷次地震中,“國資小新”推出的#抗震救災央企行動#系列,24小時跟蹤救災進展,將水、電、通信、交通、物資等方面的信息第一時間整合給公眾。近期的航母下水、中國隊1:0擊敗韓國等熱點事件中,國資委和中央企業的聲音從來沒有缺席。在日常發布方面,“國資小新”更是做到了全年365天零間斷,每一個標題都是團隊頭腦風暴、深思熟慮的結果。
“新媒體是個技術活、腦力活,更是個良心活、體力活。一分耕耘,未必一分回報,但不付出一定是無回報的。對時事的靈敏反應、獨到分析,全部要建立在大量的投入基礎之上。我已碼字三年,但依然只敢說自己是個新兵。”張灝然說。
第三句話,新媒體是市場驅動型領域,貼近用戶、注重服務是根基。張灝然表示,政務新媒體,雖具有一定媒體屬性,但其根本屬性不是媒體,而是公信力建設的“窗口”,是政民互動與服務的線上延伸,是黨和政府走“網上群眾路線”的最佳捷徑。對于政務新媒體,發布是基礎,互動是核心,服務是根本。其他類型的新媒體、自媒體也是一樣,不論是做新聞還是做營銷,不論是靠新媒體揚名還是掙錢,用戶是上帝,丟掉了這個根基,就丟掉了新媒體的紅線、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