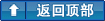我國農業保險業務規模和覆蓋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財政部10月公布的數據,2003年至2012年農業保險累計實現保費約600億元,為5.8億戶次投保農戶提供風險保障1.78萬億元。
不過,《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湖南、陜西等地調研時了解到,農業保險面臨著保費定價失靈、巨災風險大、保險公司“下鄉難”等問題。更有行業人士指出,農業保險補貼遭到一些保險公司和地方政府聯手瓜分,騙取資金等違法違規行為頻繁出現。
以往在沒有相關政策支撐下,商業性保險公司辦農業保險,在實踐中已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然而,在有了國家財政補貼以后,那些曾經制約商業性保險公司承辦農業保險的因素也仍然存在。如果這些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沒有徹底解決的話,勢必將影響到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發展后勁和前景。
農業保險補貼成為“肥肉”?
上月,中央財政提前下達2013年農業保險保費補貼預算指標56.6億元,同比增加16.7億元,增長41.9%。截至9月底,中央財政已安排撥付2012年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資金95.5億元,比2011年全年增長43.2%,帶動農業保險提供風險保障逾5000億元。
“商業保險公司過去退出農業保險,現在搶著做農業保險,就是為了補貼。”江泰保險經紀有限公司農林部首席專家郭永利說,補貼資金并沒有實實在在保障到農民頭上,反而成了一些保險公司和地方政府官員聯手瓜分的“唐僧肉”。
某商業保險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也直言,確實有的保險公司將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看作是一塊肥肉。廣東肇慶市一位曾經在商業保險公司工作過的人士說,保險公司是以盈利為目的,要有財政補貼才開辦農業保險,而且風險大的險種不做。
數據顯示,自2007年以來,中央財政已累計撥付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資金360億元。全國農險保費收入從2007年的51.84億元增至2011年8月的142億元,年均增長37.8%。
除了中央財政的補貼之外,各級財政還要安排相應的配套補貼資金。以湖南省為例,種植業保險保費中央財政補貼40%,省財政補貼25%,市縣兩級財政補貼10%,其余保費由農戶、龍頭企業或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承擔。
近幾年,農業保險被曝出的問題大多與保險補貼這塊“肥肉”有關。農業保險專家、首都經貿大學教授庹國柱表示,過去講農業保險存在道德風險,主要指的是農民騙保,事實上保險公司和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也很嚴重,農業保險成為一些保險公司和地方政府的“盛宴”,涉及地方和保險公司投機取巧、套取資金的案例很多。
2010年以來,陽光農險公司、人保財險、中華聯合財險公司在多地分支機構的案件多次被披露,涉及騙取農業保險財政補貼資金、套取糧食保險保費資金、編造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等問題。
庹國柱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講述了一個他遇到過的案例:某地保險公司與一家養豬場談農業保險業務,一頭豬100元的保費中政府補貼80元,保險公司告訴豬場負責人說只要交20元保費,保險公司再返還40元,不過一旦發生災害,保險公司不負責賠償。這樣,保險公司等于將60元的補貼裝進了自己的口袋。
庹國柱認為,農業保險成為“盛宴”,還表現為“封頂賠付”和“協議賠付”。封頂賠付是指有的地方以保費總收入的一定倍數作為賠付的上限,比如河南省是3倍封頂,浙江省是5倍封頂,這樣農民的保障水平很低,實際上是保障了保險公司利益。協議賠付是指地方政府拿財政補貼和保險公司討價還價,從中獲取一定的利益。對于這些違規行為,法律法規中應該制定限制性條款,對地方政府的違規行為在罰則里也要作出明確規定。
人保財險湖南分公司農險部總經理寧松認為,承辦農業保險是中國人保財險公司承擔的政治和社會責任,不能靠農業保險來撐規模、撐利潤。如果將農業保險作為主要的利潤來源,這是對政府、公眾和公司的“不負責”。
庹國柱說,農業保險的道德風險在任何國家都存在,不僅是企業騙取補貼,也包括農民騙保和有的地方政府套取資金等,關鍵是要制定更嚴格的制度進行防范和監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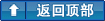
大公司能否對接小農戶?
“2007年、2008年剛開始做農業保險的時候,感覺到沒辦法完全深入到農戶中去。”寧松說,即使保險公司在縣一級設有機構,也就20個人左右,而湖南省每個縣一般都有20至30個鄉鎮,兩三百個行政村,僅靠保險公司自身力量很難實現承保和理賠到戶。
“體量巨大”的保險公司下鄉從事農業保險,如何與小農戶對接,確實是一個大問題。在從事互助保險的郭永利看來,在市場經濟中,農民本身就分散、弱小、高風險,讓他們和大保險公司來對接,兩者不對等。對于保險公司來說,他們要服務這么多的農民,存在風險高、成本高、虧損高的問題。
寧松認為,保險公司和農戶對接主要存在四個方面的難點。一是地域的分散性,像湖南戶均農田3.6畝左右,有的地方戶均才幾分田,靠保險公司收取保費,付出的成本大于收到的錢;二是農民認識的差異性,很多農民只有遇到災害才愿意投保,這是明顯的逆選擇,而保險的原則是大數法則。三是農業生產的季節性,比如湖南早稻有3000萬畝左右投保,涉及1000萬戶,而政府的貼補方案又下達得遲,保險公司必須在相應的作物生產期內完成承保服務,任務很重。四是農民對政府的依賴性。廣大農民更多的信任和依賴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災后救濟,對保險公司或多或少存在不信任感,尤其在農業保險開展初期,這種不信任和不認同感十分明顯。
人保財險長沙支公司經理助理李軍今年上半年進行水稻承保工作時,天天要下鄉宣傳介紹農業保險,嗓子都嘶啞了。他說,工作中最困惑的就是收費難,長沙縣參加水稻保險的有10萬多戶,一個家庭平均只有2.4畝農田,涉及面太廣。
理賠的問題同樣復雜,保險公司因此和農戶發生糾紛是常有的事。寧松說,農業保險的賠款,是以農作物損失的30%為起賠點,但多少是31%,多少是29%;每個作物的生長期限的賠償標準不一樣,但很多時候是在臨界點上;特別是損失特征大致相近的情況下,賠款如何平衡,公正性受到關注。由此可能出現是非,如果沒有政府行政力量和專業部門技術的參與,單獨由保險公司很難搞定。
低保費如何應對高風險?
農業保險本身屬于高風險的險種,加之我國是自然災害多發區,國內再保險市場不發達,分保方式單一,巨災保險的損失基本上只能由直接保險公司自行消化,導致難以提升巨災補償水平。
對于保險公司來說,雖然當前農業保險經營情況較好,一旦發生大的災害,這塊到嘴的肥肉可能又得“吐出來”。
陜西省楊凌區是我國唯一的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也是農業保險創新實驗區。除了奶牛,育肥豬等中央財政補貼保費的品種,2010年開始,人保財險開始在當時試點“銀保富”設施蔬菜大棚保險這一特色險種,并基本實現了全覆蓋,但兩年下來,試點效果不盡如人意。
“這個品種去年收取保費240萬元,但賠款就達到330萬元。”人保財險楊凌支公司經理余黨民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去年當地遭遇了60年一遇的連陰雨,大棚受災嚴重,導致設施蔬菜大棚保險虧損。“但這一塊沒有獲得財政上的補貼,只能用其他險種的利潤來填上這個窟窿。”
當地的情況并非個例,自然災害導致的巨額賠付是商業保險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寧松介紹,保險公司面臨的經營風險主要就是巨災風險。湖南人保8個億的農業保險保費,如果承擔的賠償責任超過3倍以上,將直接影響湖南省分公司的經營穩定性。
寧松說,不支持大幅度地降低保費,因為前幾年農業保險的經營效益不能真實地反映農業保險的本來面貌。第一是災害的周期性和損失的巨大性,災害一般10年一個大的周期,現在還沒有遇到大的災害;第二是農民的保險認知程度、維權意識在增強。
“巨災風險對保險公司的打擊很大。”庹國柱清楚地記得,他此前去加拿大考察時了解到,一家地方政府辦的保險公司從1959年到1985年的26年間經營都比較平穩,但1986年到1988年發生大旱災,導致保險公司把前二十多年積累的錢全部賠過去,還要借外債來進行賠付。
由于我國的農業巨災風險分散機制尚未建立,而再保費率高、門檻高,支持力度有限,保險公司接受的巨災風險得不到有效分散,難以提升巨災損失補償水平。對此,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郭金龍認為,應該由中央政府出資對再保險集團的經營管理費用給予補貼,或者為保險公司提供再保險補貼。同時,減免再保險業務的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
此外,對于保費的確定,地方政府和保險公司之間也有分歧,地方政府希望壓低費率,可以減少財政補貼,保險公司則擔心虧損而希望保費定得更高。郭永利說,保費制定存在定價失靈的問題,比如政府將保費定得過低,讓保險公司按商業化的辦法來經營,而保險公司接受不了這樣低的保費,只能不予推行,比如目前拖拉機交強險的參保率就不足10%。
庹國柱建議,應該成立類似美國風險管理局的這樣機構,有政府背景但保持相對獨立,負責厘定費率和起草條款,避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過去十年間,農業保險成績有目共睹,但上述農業保險覆蓋率低,保費收入不多,點多面廣,業務風險大,保險經營成本高等問題僅僅憑商業性保險公司的政治熱情顯然是解決不了的。不僅如此,在目前巨災保險缺失、相關農業保險法律法規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商業性保險公司在經營邏輯上,是否真正具有參加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熱情和沖動,同樣需要重新審視。
此外,試圖借助政策性農業保險的開展,帶動其他盈利險種的快速跟進,在目前來看,要取得效果也是不太現實的。那么,商業性保險公司在政策性農業保險上,是否真正能將之作為有效益的業務來進行開展呢?其動力何在?這些問題,還需要實踐和積累來給出一個比較明確的回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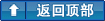
| |
鏈接一:農業保險經營主體“擴容” |
| |
保險公司和互助組織有望共同發展 |
坊間爭論不休的農業保險定位問題已有定論。10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農業保險條例(草案)》,盡管目前條例全文還沒有公布,不過消息人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與此前征求意見稿不同,即將公布的修改版本中最大的變化,是農業保險的經營主體不再限定為保險公司,而是包括了保險公司和互助保險組織等保險機構。
與半年前相比,這一進展對后者而言似乎是一個不小的勝利:《農業保險條例(征求意見稿)》自5月公布之后,一度頗多爭議之聲,尤其是對于農業保險定位和經營主體方面的內容,受到很多互助保險組織的反對。
事實上,目前農業保險領域中,商業保險公司“下鄉”這一模式面臨很多風險,補貼漏洞,人員吃緊,風險難控等問題比較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農業部門的人士提出了另一種“解決方案”,即農業保險的本質是要解決“三農”問題和保障糧食安全,農業部和財政部應該主導農業保險的發展,方向是互助合作制度,應該明確互助合作保險的法律地位。
而實踐中,互助合作保險模式也不乏成功案例。陜西省農機安全互助保險是國內現有的互助保險中開展時間較早,規模較大的涉農險種之一,由陜西省農機安全協會和農機安全監理系統聯合創辦,截至今年5月,已經在全省66個縣區開展,互助會員1.9萬名,會費收入超過500萬。
在陜西省扶風縣農機監理會并不寬敞的院子里,記者看到一塊非常醒目的“2012年農機‘三免兩補’政策”宣傳海報,上書“農機掛牌免費,農機檢驗免費,駕證換發免費,農民購買農機施行國家補貼,農機互助保險實行財政補貼”。
“我們做的是拖拉機安全互助和聯合收割(獲)機安全互助兩個保險品種,因為現在有30%至40%左右的財政補貼,縣里的農機手參與比較踴躍,目前上路運營的基本上都上了這個(互助)保險。”陜西省扶風縣農機管理服務中心主任黨軍海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由于農機安全事故頻發,保險公司要么保費極高要么不愿承保,因此大量農機手只能“裸機”冒險作業,而互助保險開展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多數“投保人”眼里,這類互助保險確實比買商業保險產品更有吸引力。“2006年買的車,當時也從保險公司買的保險,但從2010年開始以后,我就上這個互助保險了,村里大多數駕駛員都上了。”扶風縣陳關鎮秦村一組一位聯合收割機的農機手趙周乾說:“主要還是(因為)有政府補貼,比保險公司便宜,服務也挺好,有機器出事故的,賠款也很快。”
從全國范圍看,農機互助保險并不是唯一成功的案例,漁業互助保險、果樹互助保險等一大批險種已經成為所在領域的主力軍,部分險種甚至已經牢牢占據了9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這一模式與目前在農業保險市場上占絕對主力的商業保險模式的地位之爭,也成了《農業保險條例(征求意見稿)》公布后業內爭論的焦點。
據了解,《農業保險條例》的征求意見稿中將農業保險經營主體限定為保險公司,對于“互助合作保險”只字未提,對于保險公司以外的其他保險組織,規定有2年的“觀察期”,符合條件的才可繼續經營農業保險業務。
農業保險應該定位于政策性還是商業性?農業保險應該由商業保險公司主導,還是互助保險等多種組織形式共同發展?這一問題上,從不同立場和角度必然會得出不同的答案。江泰保險經紀有限公司農林部首席專家郭永利認為,互助合作保險和農民才是“門當戶對”的,通過互助共濟的辦法,做到互保、互監、互檢,達到最低的成本和最小的風險,而商業保險公司則可以承接再保險業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徐小青告訴記者,農業保險的設立是國家支持“三農”和農業現代化政策體系中的一部分,一定要體現其政策性,應該讓農業保險適應農業本身的特點,而不是讓農業來適應商業性的保險體系。政府對于互助合作保險應該給予扶持,使其逐步發展,讓農民有更多的選擇。
不過,保險行業人士普遍對此持有懷疑態度。人保財險陜西分公司一位負責人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互助保險是較為原始的保險形式,不僅“低保費、低保障”的模式在現有條件下過于理想化,而且保險產品開發,定損理賠,核算等工作也非常專業。此外,相比協會等非盈利社會團體模式主導的,公司制經營更為關系清晰便于監管,因此“只能由保險公司來做”。
中國保監會法規部主任楊華柏不久前也撰文指出,從國外的情況看,農業保險有四種不同模式,一是政府主辦的國有化模式,二是政府扶持的商業模式,三是政府支持下的國有化—商業化混合模式,四是政府支持下的互助合作保險模式。中國農業保險的經營模式和原則應是“國家支持引導、農民自愿投保、公司自主經營、政府嚴加監管”。
對此,農業保險專家、首都經貿大學教授庹國柱認為,農業保險的政策和法律法規應該早日出臺,保險公司才能有長期的打算。合作保險、相互保險有其優點,但不能因此否定商業保險公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