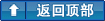隨著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近年我國(guó)電子廢棄物產(chǎn)生的速度十分驚人。據(jù)2010聯(lián)合國(guó)環(huán)境規(guī)劃署發(fā)布的報(bào)告,我國(guó)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子垃圾生產(chǎn)國(guó),每年生產(chǎn)超過(guò)230萬(wàn)噸電子垃圾,僅次于美國(guó)的300萬(wàn)噸;到2020年,我國(guó)的廢舊電腦將比2007年翻一番到兩番,廢棄手機(jī)將增長(zhǎng)7倍。電子廢棄物在回收及綜合利用過(guò)程中,不同程度存在著污染環(huán)境和損害人體健康的現(xiàn)象,亟待引起重視。
由于國(guó)家推進(jìn)“綠色照明”工程,我國(guó)第一批財(cái)政補(bǔ)貼推廣中上市的上億只老舊節(jié)能燈正進(jìn)入集中報(bào)廢期,且未來(lái)每年消費(fèi)量將超過(guò)10億只。老舊節(jié)能燈因?yàn)楹泄€U等有毒有害元素,被專家稱為是僅次于廢電池的第二大生活垃圾“汞污染源”,與之相對(duì),我國(guó)節(jié)能燈回收處理體系卻非常“幼稚”,如處置不當(dāng),污染風(fēng)險(xiǎn)不容忽視。
集中報(bào)廢威脅環(huán)境
2008年國(guó)家啟動(dòng)“綠色照明”工程,城鄉(xiāng)居民購(gòu)買使用中標(biāo)企業(yè)節(jié)能燈由財(cái)政補(bǔ)貼50%,企事業(yè)單位等大宗用戶購(gòu)買補(bǔ)貼30%。此外,還通過(guò)實(shí)施“‘光明行’公益工程”向邊遠(yuǎn)山區(qū)捐獻(xiàn)。
在此背景下展開的中國(guó)各地節(jié)能燈推廣非常迅速。如湖南省長(zhǎng)沙市2008年至2011年共推廣高效照明節(jié)能燈360萬(wàn)支,其中2011年推廣161萬(wàn)支,為湖南省發(fā)改委下達(dá)任務(wù)的2.3倍。
專家稱,考慮到首批上市的節(jié)能燈使用壽命一般為3年,據(jù)此判斷第一批財(cái)政補(bǔ)貼推廣中上市的上億只節(jié)能燈正進(jìn)入集中報(bào)廢期。
長(zhǎng)沙市兩型辦主任吳德峰告訴《經(jīng)濟(jì)參考報(bào)》記者,節(jié)能燈比普通白熾燈節(jié)電80%,全市推廣360萬(wàn)支節(jié)能燈,年節(jié)電約1.79億度,減排二氧化碳17.1萬(wàn)噸。而根據(jù)國(guó)務(wù)院發(fā)布的節(jié)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國(guó)家“綠色照明”工程通過(guò)財(cái)政補(bǔ)貼的方式向全國(guó)推廣高效照明產(chǎn)品1.5億只,一年可累計(jì)節(jié)電290億千瓦時(shí),少排放二氧化碳2900萬(wàn)噸、二氧化硫29萬(wàn)噸。
在長(zhǎng)沙、北京等地沃爾瑪、家樂(lè)福等超市,節(jié)能燈琳瑯滿目。在一些國(guó)際品牌的包裝盒里,有張被折成小方塊的說(shuō)明書。在這張紙片背面或者一角,附有一張有毒有害物質(zhì)和元素表,顯示節(jié)能燈毛管、燈頭、鎮(zhèn)流器、塑料件四大構(gòu)成部分不同程度存在鉛、汞、多溴聯(lián)苯等有毒有害元素。按照信息產(chǎn)業(yè)部發(fā)布的《電子信息產(chǎn)品中有毒有害物質(zhì)的限量要求》,有的螺旋形電子節(jié)能燈毛管中的鉛、汞,鎮(zhèn)流器中的鉛,塑料件中的多溴聯(lián)苯、多溴二苯醚超標(biāo);而有的節(jié)能燈則在毛管、燈頭、鎮(zhèn)流器全部鉛超標(biāo),毛管中汞超標(biāo)。
長(zhǎng)沙市兩型辦綜合處介紹,相關(guān)研究表明,廢舊節(jié)能燈特別是老式熒光管中汞含量平均約0.5毫克,僅夠沾滿一個(gè)圓珠筆尖。但若滲入地下后,足以污染約180噸水及周圍土壤。此外,廢棄的節(jié)能燈管破碎后,瞬時(shí)可使周圍空氣中的汞濃度嚴(yán)重超標(biāo)。一旦進(jìn)入人體,可能破壞人的中樞神經(jīng)。
有業(yè)界專家認(rèn)為,隨著白熾燈逐步消亡,我國(guó)年消費(fèi)量可達(dá)10多億只。雖然近年來(lái)技術(shù)不斷進(jìn)步,節(jié)能燈汞污染等問(wèn)題大大減輕。但就早期生產(chǎn)的節(jié)能燈來(lái)看,很多產(chǎn)品因?yàn)楫?dāng)初的工藝技術(shù)比較落后,汞污染等問(wèn)題比較突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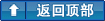
回收渠道匱乏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環(huán)境學(xué)院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管理系主任靳敏說(shuō),推廣節(jié)能燈實(shí)現(xiàn)了節(jié)能減排,但“用起來(lái)很節(jié)能、收回去沒(méi)渠道”已成當(dāng)今電子廢棄物突出問(wèn)題之一。
《經(jīng)濟(jì)參考報(bào)》記者近期在北京、武漢等地走訪,發(fā)現(xiàn)無(wú)論是超市還是廢品回收站,廢舊節(jié)能燈“白給也不要”。北京一家燈飾店老板說(shuō),曾有企業(yè)搞公益回收,卻被人認(rèn)為要把節(jié)能燈收去翻新再賣。節(jié)能燈回收箱要墊海綿,運(yùn)輸?shù)眯⌒囊硪恚慊厥占兇狻百r本兒賺吆喝”!
一家照明企業(yè)業(yè)務(wù)經(jīng)理說(shuō),在中部一些大城市社區(qū)開展的公益活動(dòng),往往半天也收不回幾只節(jié)能燈,而垃圾桶、垃圾站里混在雜物中的廢舊節(jié)能燈時(shí)常可見(jiàn),被當(dāng)成普通生活垃圾被送填埋場(chǎng)或焚燒處理。無(wú)奈,活動(dòng)組織者只好告誡居民不能將廢舊節(jié)能燈敲破,不能給小孩玩,套個(gè)塑料袋再扔。
上海電子廢棄物交投中心擁有一套年處理廢舊節(jié)能燈1700噸進(jìn)口裝置,在國(guó)內(nèi)非常罕見(jiàn)。在這類處理線上,佩戴防護(hù)裝備工作人員把廢舊節(jié)能燈送進(jìn)處理設(shè)備后,經(jīng)粉碎、汞吸收等工序回收。據(jù)了解,上海電子廢棄物交投中心一位工作人員嚴(yán)重“吃不飽”,主要靠一些機(jī)關(guān)單位送點(diǎn)廢舊燈管過(guò)來(lái)。
需多管齊下
長(zhǎng)沙市再生資源協(xié)會(huì)秘書長(zhǎng)周儆提供的資料顯示,與中國(guó)“一扔了之”相比,日本、歐美、臺(tái)灣地區(qū)廢舊節(jié)能燈回收率達(dá)80%以上。周儆等人赴臺(tái)灣考察看到,“中國(guó)電器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中臺(tái)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了一個(gè)制造、銷售和回收廢棄照明光源循環(huán)體系,汞、熒光粉、玻璃的回收利用率分別達(dá)100%、60%和30%。在地方公告應(yīng)回收項(xiàng)目(照明光源類)管理基金補(bǔ)貼下,“中國(guó)電器”處理社區(qū)上繳廢燈管生產(chǎn)線保持著正常負(fù)荷運(yùn)行。
相關(guān)專家結(jié)合海外經(jīng)驗(yàn),建議未來(lái)推進(jìn)廢棄節(jié)能燈回收從三個(gè)方面入手:
一是大力宣傳廢節(jié)能燈不能“一扔了之”。雖然節(jié)能燈2008年就被納入《國(guó)家危險(xiǎn)廢物名錄》,但社會(huì)至今仍只知其節(jié)能之利、不知污染之害。為此,要加大宣傳力度樹立節(jié)能燈作為“危廢”嚴(yán)禁隨意丟棄和非法處理的社會(huì)共識(shí)。
二是強(qiáng)化生產(chǎn)者環(huán)境責(zé)任。目前,我國(guó)“電子信息產(chǎn)品中有毒有害物質(zhì)的限量要求”屬于行業(yè)性推薦標(biāo)準(zhǔn)沒(méi)有強(qiáng)制力,為此可探索率先在節(jié)能燈這類“危廢”電子產(chǎn)品領(lǐng)域率先建立強(qiáng)制性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切實(shí)降低污染,同時(shí)要求廠商在廣告、產(chǎn)品包裝、銷售現(xiàn)場(chǎng)醒目警示污染風(fēng)險(xiǎn)。
三是加大財(cái)政介入力度。從一些先進(jìn)國(guó)家和地區(qū)經(jīng)驗(yàn)看,廢舊節(jié)能燈回收有銷售市場(chǎng)、社區(qū)和民間環(huán)保組織三種渠道。鑒于節(jié)能燈易碎、資源回收利用價(jià)值低且處理成本高,國(guó)家應(yīng)將其回收利用納入財(cái)政支持范疇。要制定實(shí)施細(xì)則扶持社區(qū)、企業(yè)、環(huán)保公益組織設(shè)立固定回收點(diǎn);對(duì)居民上繳廢燈給予物質(zhì)鼓勵(lì);把節(jié)能燈推廣財(cái)政補(bǔ)貼與中標(biāo)單位建立回收機(jī)制相掛鉤;對(duì)企業(yè)和中心城市在合理規(guī)劃范疇內(nèi)建立無(wú)害化處理中心,給予財(cái)稅扶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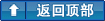
| |
鏈接一:泛濫成災(zāi) 充電器變身“環(huán)境殺手” |
在深圳工作的仰雙全家有一個(gè)專門擺放各類充電器的儲(chǔ)物盒。其中,僅手機(jī)充電器就有6個(gè),它們接口互不相同:自己使用的iPhone特有的30針dock接口和諾基亞常用的細(xì)口,女朋友的三星手機(jī)是Micro-USB接口,還有一部閑置的聯(lián)想功能性手機(jī)使用的是mini-USB接口,另外兩個(gè)充電器是過(guò)去使用的手機(jī)或丟了或壞了而閑置下來(lái)的,一個(gè)諾基亞粗口的和一個(gè)索愛(ài)手機(jī)的。
據(jù)介紹,手機(jī)充電器主要分為線充和座充兩種,而以線充的充電接口作區(qū)分,目前,市面上存在的充電器多達(dá)30多種,如今仍常用的約12種,即使接口相同,電壓和電流可能還不同,實(shí)際種類就更多了。
工信部今年3月底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guó)手機(jī)用戶已突破10億戶。以每個(gè)用戶平均3年更換一次手機(jī)的頻率計(jì)算,每年被替代的手機(jī)將達(dá)3.3億部。這也意味著,每年閑置出來(lái)的手機(jī)充電器超過(guò)3億個(gè)。
與手機(jī)充電器同樣“泛濫”的還有筆記本電腦的電源適配器。據(jù)業(yè)內(nèi)權(quán)威的市場(chǎng)研究機(jī)構(gòu)最新數(shù)據(jù),2012年全球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出貨量達(dá)3.3億臺(tái)。
在廣州太平洋電腦城從事PC銷售6年的陳淙淙介紹說(shuō),市面上主流的聯(lián)想、惠普、索尼、戴爾等品牌的筆記本電腦的電源適配器基本上不能通用,它們接口各異,更重要的是,電壓和電流不同,一般情況下聯(lián)想thinkpad的輸入電壓是20V,戴爾有19.5V也有20V,惠普一般是18.5V,索尼則是19.5V。
即使同一品牌,也因?yàn)榕渲貌煌娫催m配器的電壓和電流也大小各異。
國(guó)際電聯(lián)的一項(xiàng)研究顯示,制造一部手機(jī)充電器的材料重量約占手機(jī)和充電器總重量的20%-30%。這意味著,廢舊手機(jī)充電器中所含有的貴金屬和可再生資源的數(shù)量相當(dāng)可觀。
陳淙淙說(shuō),且不說(shuō)充電器泛濫帶來(lái)的巨大資源浪費(fèi),對(duì)個(gè)人消費(fèi)者而言,這也是巨大的浪費(fèi)。目前,一部手機(jī)充電器的價(jià)格約在50元至150元不等,而筆記本電腦的電源適配器就高達(dá)四五百元。以手機(jī)充電器為例,按每年被替代3.3億個(gè)計(jì)算,也就相當(dāng)于消費(fèi)者的財(cái)產(chǎn)損失最多達(dá)500億元。若每個(gè)充電器約30g,那么就意味著一年產(chǎn)生的電子垃圾近萬(wàn)噸,并因此產(chǎn)生300萬(wàn)噸溫室氣體。
中山大學(xué)環(huán)境科學(xué)與工程學(xué)院教授李適宇說(shuō),盡管人們對(duì)電子垃圾對(duì)水體和土壤,進(jìn)而對(duì)人體的危害已經(jīng)有所認(rèn)知,但充電器的危害卻往往被忽略。和大多數(shù)電子垃圾的成分類似,廢舊充電器中也含有汞、鎘、鉛等重金屬和廢塑料,它們都是水體和土壤污染的主要?dú)⑹帧?BR> 以色列國(guó)家環(huán)保部最新研究表明,長(zhǎng)時(shí)間與充電器接觸,易增加罹患癌癥風(fēng)險(xiǎn)。負(fù)責(zé)該項(xiàng)研究的科學(xué)家說(shuō),因夜晚休息時(shí)人體不會(huì)分泌可減輕輻射線危害的黑色激素,若臥室甚至床頭旁放著充電器,最容易對(duì)人體造成危害。若未保持半米以上的安全距離,手機(jī)專用的充電器等所散發(fā)的輻射,將使人體如同暴露在高壓電源線底下。
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于志強(qiáng)表示,盡管相關(guān)研究還未能完全獲得臨床驗(yàn)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手機(jī)充電器、筆記本電源適配器等含有變壓器的電子垃圾輻射超過(guò)了電腦和手機(jī)本身,應(yīng)及時(shí)處理。正因?yàn)槠湮:υ诂F(xiàn)階段不能完全清楚知曉,加上越來(lái)越龐大的數(shù)量,這一潛在的風(fēng)險(xiǎn)更加不容忽視。
《經(jīng)濟(jì)參考報(bào)》記者在廣州、北京等采訪發(fā)現(xiàn),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不知如何處置閑置充電器的煩惱”:新舊經(jīng)常弄混,家庭成員之間也常常分不開哪個(gè)充電器是自己的。在廣州太平洋電腦城、深圳華強(qiáng)北電子城及北京中關(guān)村等電子產(chǎn)品集中地,與目前廢舊手機(jī)回收相比,充電器的回收明顯滯后,不可能與手機(jī)一起進(jìn)入二手市場(chǎng)或廢舊市場(chǎng)被再利用。
專家建議,盡快修改充電器國(guó)標(biāo)以實(shí)現(xiàn)充電器標(biāo)準(zhǔn)的完全統(tǒng)一,并通過(guò)實(shí)施“機(jī)充分離”,減少重復(fù)生產(chǎn)和消費(fèi)。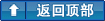
遼寧省沈陽(yáng)市梅江東社區(qū)的張慧梅熱心環(huán)保事業(yè),3年時(shí)間回收了近500千克的廢舊電池,卻面臨無(wú)處可送的境地。長(zhǎng)沙市人民中路長(zhǎng)鑫花園小區(qū)秦秦小朋友從電動(dòng)玩具、遙控器等小家電中攢了3公斤廢電池,也不知往哪送。
電子產(chǎn)品普及的同時(shí),作為電子產(chǎn)品必備配件的電池也快速增長(zhǎng),年報(bào)廢量已達(dá)95萬(wàn)噸。電池中含有鉛、銅、鋰、鋅、錳、鎘、鎳和鈷等金屬,具有較高回收價(jià)值。但是,在我國(guó),廢舊電池回收潛力巨大卻遭遇尷尬。
專家指出,經(jīng)過(guò)二十余年努力,回收廢舊電池的環(huán)保觀念已經(jīng)被多數(shù)人所接受。但是,個(gè)人熱心無(wú)處可送,企業(yè)回收獨(dú)木難支。目前許多地方的政策都是“不鼓勵(lì)不反對(duì)”,這容易挫傷社會(huì)公眾參與環(huán)保的積極性,也讓電池回收處于尷尬境地。為環(huán)保考慮,如果把這種閑散的民間回收行為變成系統(tǒng)的政府主導(dǎo)、企業(yè)運(yùn)作、社會(huì)參與的行為,電池良性循環(huán)就能實(shí)現(xiàn)。
電池集中回收與否一直存在爭(zhēng)論。一派觀點(diǎn)認(rèn)為,按國(guó)家要求,現(xiàn)在禁止生產(chǎn)汞含量大于電池重量0.0001%堿性鋅錳電池,干電池基本實(shí)現(xiàn)無(wú)汞;日常生活產(chǎn)生的廢鎳鎘、氧化汞電池不按危險(xiǎn)廢物管理,可分散與生活垃圾一并處理,不會(huì)造成環(huán)境污染;現(xiàn)行條件不鼓勵(lì)集中收集處理。
這種觀點(diǎn)的依據(jù)是,2003年10月9日,原國(guó)家環(huán)境保護(hù)總局、國(guó)家發(fā)展與改革委員會(huì)、原建設(shè)部、科學(xué)技術(shù)部和商務(wù)部聯(lián)合發(fā)布的《廢電池污染防治技術(shù)政策》(以下簡(jiǎn)稱《技術(shù)政策》)。其中指出:“廢一次電池的回收,應(yīng)由回收責(zé)任單位審慎地開展。目前,在缺乏有效回收的技術(shù)經(jīng)濟(jì)條件下,不鼓勵(lì)集中收集已達(dá)到國(guó)家低汞或無(wú)汞要求的廢一次電池。”
北京師范大學(xué)化學(xué)學(xué)院博士后毛達(dá)卻認(rèn)為,這一規(guī)定有其合理之處,但在實(shí)際工作中,一些地方環(huán)保官員往往將之模糊地轉(zhuǎn)述為“國(guó)家已經(jīng)不鼓勵(lì)收集日常生活中產(chǎn)生的廢電池”,并以此回應(yīng)公眾的疑惑。但是,他們?cè)诒磉_(dá)此觀點(diǎn)的時(shí)候,往往不會(huì)提及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著的一些危險(xiǎn)性廢電池(如含汞扣式電池、含鎘充電電池)應(yīng)該如何處置。
根據(jù)《技術(shù)政策》要求,我國(guó)2005年1月1日起停止生產(chǎn)含汞量大于0.0001%的堿性鋅錳電池。目前,我國(guó)電池的用汞量呈逐步降低的趨勢(shì)。但是,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xué)研究所程和發(fā)研究員的研究表明,從1995年至2009年,中國(guó)電池產(chǎn)業(yè)的用汞量已從每年582.4噸降至140噸。廢電池的含汞量大幅下降,但仍占生活垃圾含汞總量的54%,仍是我國(guó)含汞最多的生活垃圾。
有業(yè)內(nèi)人士指出,干電池基本無(wú)汞是理想狀態(tài),雖然大電池企業(yè)生產(chǎn)的電池目前都做到了低汞化或無(wú)汞化,但大量小企業(yè)生產(chǎn)的電池還存在高汞現(xiàn)象,許多假冒偽劣低價(jià)一次干電池的含汞量也可能超過(guò)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
毛達(dá)認(rèn)為,無(wú)汞化或低汞化政策不足以控制廢電池重金屬污染。目前,大量含汞紐扣式電池和低汞一次干電池仍然被大量生產(chǎn)或使用。鎳鎘電池產(chǎn)量仍達(dá)4億只,存在類似汞的鎘污染風(fēng)險(xiǎn)。考慮到我國(guó)混合垃圾的末端處置場(chǎng)所,如垃圾填埋場(chǎng)和焚燒廠的污染防治還處在不高的水平,將廢電池所含的有害物質(zhì)集中留到末端進(jìn)行治理,風(fēng)險(xiǎn)很高。
專家指出,經(jīng)過(guò)多年環(huán)保觀念培育和技術(shù)進(jìn)步,我國(guó)應(yīng)當(dāng)與時(shí)俱進(jìn),借鑒國(guó)外經(jīng)驗(yàn),建立健全廢舊電池回收體系和相關(guān)法規(guī),支持行業(yè)發(fā)展,開發(fā)城市礦山,變廢為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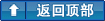
經(jīng)一位走街串巷的“破爛王”指點(diǎn),《經(jīng)濟(jì)參考報(bào)》記者在距中關(guān)村不遠(yuǎn)的海淀區(qū)石板房南路一側(cè),找到了一個(gè)十分繁忙的收購(gòu)、翻新、銷售舊家電的市場(chǎng)。大門一側(cè)空地上,有位女店主戴著手套將浸透了化學(xué)清洗劑的衛(wèi)生紙,像女士敷面膜一樣緊緊貼在舊的分體空調(diào)室內(nèi)機(jī)上,曬干后將“面膜”一揭,空調(diào)塑料殼立即變得光鮮如新。彌漫著一股塑料味和化學(xué)藥劑味兒的市場(chǎng)里,舊家電垛成的“小山”間,有不少出租房屋、開小旅店的人光顧。
而在北京華新綠源環(huán)保產(chǎn)業(yè)有限公司廠區(qū),記者看到,停止運(yùn)轉(zhuǎn)的生產(chǎn)線上只有幾名工人在做維護(hù)保養(yǎng)。這還是目前北京市唯一列入國(guó)家廢棄電器電子產(chǎn)品處理基金補(bǔ)貼的企業(yè)。該公司總經(jīng)理王建明說(shuō),由于國(guó)家“基金補(bǔ)貼”運(yùn)行細(xì)則尚未出臺(tái),公司的家電拆解線暫時(shí)停產(chǎn)。據(jù)了解,北京市每年產(chǎn)生的各種廢舊電器總量約600萬(wàn)臺(tái)(套),而公司去年業(yè)務(wù)最高峰期“四機(jī)一腦”拆解量只有180萬(wàn)臺(tái),大量電子廢棄物流向了二手市場(chǎng)和“作坊拆解”。
在長(zhǎng)沙、武漢等城市,二手電器市場(chǎng)都很“火”。店主和雇工們?cè)诖擞酶腻F、鉗子等工具先敲敲打打拆解,從散亂的零部件中選取有使用價(jià)值的組裝“二手電器”。無(wú)法修復(fù)的破機(jī)殼、銹喇叭、斷裂電源線、破損線路板等,有的扔掉或付之一炬,有的銷往“下游”。
廣東省汕頭市貴嶼鎮(zhèn)擁有5000多個(gè)家庭拆解作坊、超過(guò)10萬(wàn)人從業(yè),是國(guó)內(nèi)外電子垃圾的“下游終點(diǎn)”之一。《經(jīng)濟(jì)參考報(bào)》記者6月在當(dāng)?shù)夭稍L時(shí),發(fā)現(xiàn)這里的部分河溝水黑如墨,空氣中不時(shí)彌漫著酸腐或者塑料燒焦的味道。鎮(zhèn)里到處是電子垃圾回收站和掛著各式各樣招牌的廢舊電子配件店鋪,路上滿是大小貨車滿載廢舊電子物品穿行。貴嶼鎮(zhèn)村民李偉明說(shuō),20多年來(lái),拆解電子垃圾為常年內(nèi)澇的貴嶼人解決了生計(jì)問(wèn)題,很多人還借此成為千萬(wàn)甚至億萬(wàn)富翁。
在貴嶼鎮(zhèn)一個(gè)小作坊,記者見(jiàn)識(shí)了當(dāng)?shù)厥⑿械摹巴跛嵯捶ā保簝H有手套和口罩防護(hù)的工人們把芯片、電路板等浸泡在不同的強(qiáng)酸溶液中,“洗”出包括黃金、白銀等在內(nèi)的各種金屬,但也產(chǎn)生直排大海的大量含重金屬、有毒化學(xué)物質(zhì)的廢水,揮發(fā)大量直接排入空中的有毒氣體。在這里,還有人用火烤線路板、用火燒電線電纜。一天跑下來(lái),人會(huì)變得“灰頭土臉”,白天吸入鼻孔的大量酸臭味兒讓人連喝水都感到惡心。
當(dāng)?shù)馗刹扛嬖V記者,貴嶼鎮(zhèn)2006年便開始籌備建設(shè)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園區(qū)治理污染。但時(shí)至今年6月,規(guī)劃為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園區(qū)的土地仍然空空如也。當(dāng)?shù)厝罕姺Q6年來(lái)看了兩次所謂“奠基開工”,但園區(qū)就是沒(méi)建成。
在國(guó)內(nèi)一些“非法拆解”泛濫之地,總有人訴苦說(shuō),小作坊多如牛毛且很隱蔽,而政府負(fù)責(zé)監(jiān)管的只有幾個(gè)人,根本管不過(guò)來(lái)。但從臺(tái)州、肇慶等地實(shí)踐看,地方和監(jiān)管部門靠從如下層面入手治住了“小拆解”:
一是要構(gòu)建“環(huán)境保護(hù)網(wǎng)格化管理體系”。圍繞治理目標(biāo),基層組織中村居(社區(qū))層面,可推行環(huán)保聯(lián)絡(luò)員制度;在鄉(xiāng)鎮(zhèn)(街道)乃至區(qū)縣(市)層面,則要明確各級(jí)行政一把手是轄區(qū)環(huán)境質(zhì)量管理第一責(zé)任人,訂出年度目標(biāo)考核實(shí)行“一票否決”。
二是要用聯(lián)動(dòng)機(jī)制破除“九龍治水”。要以環(huán)境整治協(xié)調(diào)機(jī)構(gòu)為主體,統(tǒng)一指揮并令行禁止。
三是制度設(shè)計(jì)要健全。這既要培育好新興產(chǎn)業(yè)吸納人員轉(zhuǎn)崗就業(yè),更要圍繞長(zhǎng)效機(jī)制建立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責(zé)任制、減排工作目標(biāo)責(zé)任、河流交接斷面水質(zhì)考核辦法、聯(lián)合執(zhí)法和案件移送制度、環(huán)境違法企業(yè)停水停電制度、綠色信貸管理辦法、信用評(píng)級(jí)制度、環(huán)境信息互聯(lián)互通等制度。